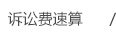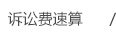保险消费者信息提供义务与民事欺诈规范再造
一、问题的提出: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行使可否纠纷案的频发与挑战
近些年来,围绕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间的私法冲突的争议与纠纷层出不穷,引起了立法、司法实务界以及法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就立法而言,作为“准立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3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稿)》第9条以及2014年10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公开征求意见稿)》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保险人的“欺诈撤销权”。但在最终通过的司法解释中,因争议较大而取消了此条规定。学界对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间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就司法实践而言,由第三人代为投保、带病投保等类型的保险投保欺诈案件也频繁出现,日益引起人们关注。[1]由此观之,“欺诈撤销权”问题无法回避:一方面,对于保险人是否可以行使撤销权,各级法院在裁判类似案件时呈现出不同观点;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和保险法理论界对于“欺诈撤销权”的态度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影响着保险目的的实现,也在保险诉讼实务中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从法律角度而言,保险是一种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其属于民商事合同的一种,是故适用民法中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并无疑问。鉴于保险的特殊商品属性,适用欺诈、违反公序良俗等一般规定,更加有利于发挥防范投保欺诈的功能。[2]告知义务作为保险人进行风险选择的必要制度,即便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不当然会导致保险人在意思表示上的瑕疵。但如若违反告知义务被认定,投保人的欺诈行为有可能满足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的要件。在此情况下,保险人除了可以主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是否亦可根据《民法典》第148条主张对因受欺诈所订立合同的撤销权?[3]如果承认基于欺诈的撤销权,则在未满足《保险法》所定要件无法主张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可能基于民法上的欺诈制度而主张免责。依此逻辑,保险人根据违反告知义务和欺诈等制度均可摆脱合同的约束,在效果上存在重合。在此情况下,如何理解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就成为重要问题。
从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来看,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必须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并保证告知的真实性。若投保人违反该义务,则会产生保险合同的解除或保险人免责等不利于投保人利益的后果。其理由在于,保险的基本原理是“对价平衡”。亦即,保险人根据单个保险合同承担的风险程度评估保费,对于超过一定程度的风险将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人评估和同意承保与否的相关信息,对风险程度进行判断是十分必要的(风险选择)。然而,由于这些信息具有单方性且不对称地由投保人一方掌控,保险人要获得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需要接受投保人一方的告知。[4]进而,“保险的本质属性及其信息不对称之特质决定了保险人容易陷入对抗保险欺诈之困境”。[5]鉴于保险人技术评估上的必要性,保险法承认投保人有向保险人提供作为信息提供义务的告知义务。[6]
是故,当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没有满足保险法中的规定,例如超过《保险法》规定的两年抗辩期限而不能主张权利时,保险人有可能通过主张投保人存在民法上认识错误或欺诈的意思表示瑕疵以实现免责的效果。其理由在于,在此情况下,投保人一方的恶意较强。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关于此种情形下不排除成立欺诈的规定,[7]对我国也可能产生了影响。[8]由于我国《保险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当投保人不实告知行为如果符合《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撤销权行使要件,则保险人是否可以根据该条规定行使撤销权?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中,对于如何理解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问题,长期存在争议。[9]我国多数保险法学者及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者支持将意思表示瑕疵中的错误和欺诈分别对待,采“错误排除说”立场。“如果投保人以欺诈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除可以根据《保险法》规定解除合同外,亦可根据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撤销合同;如若投保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则保险人仅可根据《保险法》规定寻求救济。”[10]持“错误排除说”立场者进一步认为,在《保险法》修改时,应引入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欺诈撤销权”的规定。[11]“当然,实践中应谨慎适用该规定,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保人实施欺诈行为订立合同的,才可允许保险人撤销合同。”[12]但学界并未对“欺诈”的理念予以充分诠释。尤其是在研究告知义务制度与意思表示瑕疵的关系时,告知义务制度规定的投保人保护的理念究竟应涵摄至何种程度?具言之,既然我国《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欺诈可撤销制度均是为解决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3]则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其是否负有信息提供义务及其范围就是决定告知义务制度与欺诈可撤销制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因素。[14]但是,我国学界对此问题鲜有涉及。因此,在讨论是否引入此“药方”或另辟蹊径时,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深入挖掘,才能精准解决我国的相关问题。本文以上述论点为基础展开讨论,拟厘清德、日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处理经验,对我国《保险法》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典》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关系进行妥当的定位。
二、保险立法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冲突的排除:立场与规则
(一)国外保险立法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冲突之缘起:理论分歧
1.德国法
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第1款第1句明文规定了投保人的“无限告知义务”,[15]该义务为“不真正义务”(obliegenheit)。在投保人违反该义务时,该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其“仅在以欺诈意图隐瞒保险人未书面询问之重要危险情况时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然而,第22条与第18条第2款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之解除权规则不同,该条设置了保险人享有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权。[16]就告知义务的构造相关规则来看,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在全面修改时基本沿袭了旧法的法律框架,规定了如下内容:其一,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欺诈撤销权)删除了以欺诈为由的保险人合同撤销权之“因危险事实”一语,但并未改变其中心理念;[17]其二,对于告知义务的模式,鉴于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正当利益,尤其是该条第1款规定的将“危险事实”是否重要交由投保人来评价会使其承担不合理的风险。亦即,对投保人而言,判断某些事实是否属于重要风险并非易事,因此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采取了“文字询问应答义务”主义(第19条第1款第1句),[18]但就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增设了排除恶意投保人的请求权规定(第21条第2款第2句),即“投保人意图欺诈而违反告知义务,则保险人不负赔付义务”,并将投保人欺诈时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延长至10年(第21条第3款)。
学者对全面修改后的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与欺诈撤销权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分歧。根据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投保人就危险事实实施欺诈行为的,保险人可以根据《德国民法典》中欺诈相关规定撤销保险合同。有学者认为,保险人对此等保险合同的撤销权不限于投保人积极实施虚假告知的情况,就仅对危险事实进行隐瞒的情况(沉默欺诈)时亦可适用。[19]不过,投保人构成“沉默欺诈”须以有责任将该沉默事实告知对方的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20]迄今为止取得的广泛一致的观点是,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即相当于此种义务。[21]
与1908年旧法不同,根据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款的规定,投保人仅对保险人采用“文字方式”(in Textform)询问的事实负告知义务。因此,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一方面继续承认在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不实告知时保险人可适用欺诈相关规定,但另一方面对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未询问事实规定其不发生告知义务。因此,保险人是否可以沉默欺诈为由行使保险合同撤销权,就成为重要问题。关于此点,德国立法者指出:投保人对保险人完全没有询问或者仅以口头方式询问的与危险有关的重要情况的沉默,在其具有恶意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的“欺诈撤销”规定作为保险人行使撤销权的基础,即使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时,仍可以作为撤销保险合同的前提而存在。[22]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若投保人对“重要事实”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且具有恶意投保欺诈之意图,则保险人仍可基于欺诈行使保险合同的撤销权。[23]但德国保险法理论学界对此问题持正反两种观点。
一是“沉默欺诈否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法既然仅对保险人在明确提出询问时投保人才发生告知义务予以规范,则对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的情况下,其不发生告知义务,保险人不可以以欺诈为由行使撤销权。该观点进一步认为,作为投保人构成沉默欺诈基础之“作为义务”,保险人亦不可援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之信息提供义务主张权利。其理由在于,保险合同法规定的危险相关重要事实之告知义务具有排他性的特别法规则之属性。[24]由上可知,对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是否构成沉默欺诈时,学者旨在通过否定作为义务的存在为投保人提供救济途径。
二是“沉默欺诈肯定说”。持该立场的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即使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保险合同法亦不排除保险人以沉默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可能性。此结论是从保险合同法中承认保险人就危险事实欺诈的撤销保险合同之规定中直接推导出来的。[25]但如前所述,“沉默欺诈否定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投保人的作为义务之法律基础,无法成立沉默欺诈。正因为如此,多数学者另辟蹊径,以对危险事实的评价为主线,私法冲突问题的解决路径从两者的“排除论”转向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的“交互作用论”。因此,承认保险人行使欺诈撤销权的前提是,投保人除负有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外,还负有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信息提供义务。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投保人负有向保险人履行危险事实之信息提供义务,且该义务不被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规定所排除。
2.日本法
众所周知,与1899年《日本商法典》中的规定相比,2008年新制定的《日本保险法》中,以告知义务为代表的诸多规定更加强调对投保人一方的保护。[26]以生命保险(人身保险)为例,该法第37条采“询问应答义务”主义立场。[27]在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上,《日本保险法》和1899年《日本商法典》相同,均以投保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构成要件,承认保险人的解除权。[28]
关于《日本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以及其与《日本民法典》中的错误、欺诈制度的适用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日本判例的立场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不确定时期。现今日本判例通说采“错误规定排除说”立场。[29]其中,1993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判決为“错误规定排除说”奠定了基调。该案案情为:投保人在订立海外旅行伤害保险合同时,未向保险人告知被保险人腹部有大动脉瘤的事实。最高裁判所判决指出,即使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即患病事实)存在错误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但也仅仅是“动机错误”,然而该动机并没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不足以评价其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要素产生了错误认识(即要素的错误)。[30]尔后,对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欺诈行为,日本裁判所通常认为,只要满足民法总则或告知义务制度中的欺诈要件,保险人就可以主张该保险合同无效。[31]也就是说,即使除斥期间经过后,保险人仍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该保险合同无效。[32]关于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日本通说亦采大审院判决的立场。如此一来,在判例和学说中,可以说不必对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其主观恶性较强的投保人予以保护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是故,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权,保险人可以拒绝向投保人支付保险金。[33]在保险人以投保人欺诈为由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返还保险费的义务。[34]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承认保险人行使欺诈撤销权的前提,在主观要件上因应存在欺瞒对方之意图,违反告知义务并不必然构成欺诈。[3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尽管不排除欺诈可撤销权的适用,但需遵照告知义务制度的中心理念,对判断投保人是否构成欺诈的构成要件加以限制(以下简称“告知义务制度限缩解释说”)。[36]具言之,如若承认欺诈的成立,欺瞒行为应当存在违反社会常识的违法性,即谓“违法性欺瞒行为”。[37]是故,有学者主张,可以将“违法性”这一规范要件理解为是保险法上之要求。[38]
(二)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的交互作用:构成要件之视点
如上所述,德国部分学者主张,即使不考虑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询问应答义务化问题的影响,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主流观点赞同德国观点,认为限缩解释具有合理性。[39]换言之,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对象之事实范围比告知义务的对象事实范围要窄。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投保人告知义务对象的“重要事实”相当宽泛,将其对此类事实的未告知直接评价为其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信息提供义务不具合理性。[40]
其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对象事实是与保险事故发生之可能性的“重要事实”。这里所述的重要事实是指,保险人若知晓该事实,则不会作出同意承保的决定,或者将会设定更高的保险费费率等事实。[41]亦即,是与保险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判例和学说通常将“该事实是否对保险人进行危险选择产生影响”作为重要性的判断标准。[42]就投保人在同一事实范围内是否承认提供信息的义务而言,由于信息提供义务是确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基础,因此在投保人履行信息提供义务的对象事实中包含与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是没有意义的。此外,鉴于信息提供义务应当是“个人为自己收集信息”的私人自治原则,或者该义务是对“自我原则”的修正,因此不应当无限地扩大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
其三,从至今为止的判例来看,裁判所仅在构成要件极为严苛的前提下,才承认保险人以欺诈为由的合同无效或合同撤销权。[43]事实上,在大多数判例中,就一般论而言,裁判所不仅没有采取排除欺诈规定适用的立场,反而实际上承认了保险人欺诈撤销权的行使。[44]尤其是在对于投保人成立欺诈应当具备的逻辑前提,即如果保险人知悉,则当然不会订立合同的重要事项,然而投保人却未告知;以及判例对投保人作出与保险人是否订立合同相关之“相当重要的事实”未如实告知的强调,采取的可谓是一种限缩解释之立场。该立场是判例在事实上对学者所倡导的“告知义务制度限缩解释说”的进一步确认。换言之,仅在投保人对极其重要的事实未向保险人告知或不实告知的情况下,才承认保险人欺诈撤销权的适用。即在理论上,投保人对危险事实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极为有限。[45]这种判断与德国学说中认为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范围一致。
三、法律适用规范冲突解决路径: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
在德、日保险法理论中,学者在承认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讨论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是否比告知义务中的事实范围要窄,抑或是尽管告知义务规定不完全排除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然而采“文字询问应答义务”主义的告知义务制度是否会影响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以上所述内容都涉及信息提供义务对象的“事实范围”,但其说理并不相同。
第一,关于信息提供义务对象之事实范围问题,部分学者主张,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范围仅在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才发生。主流观点认为,从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修改前的投保人“主动告知义务”主义下的相关判例来看,就重要事实而言,投保人一方面对保险人未提出询问事项应当承担主动的告知义务;但另一方面,如果保险人采用“询问表”方式,对于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的,则仅在投保人存在恶意时保险人才发生解除权(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8条第2款)。在围绕“主动告知义务”这一问题的相关案件中,法院通常不从投保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角度进行判断,而是通过否定成为问题事实的重要性的角度进行处理。换言之,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投保人仅在应当告知之事实对其而言是“不言而喻”这种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才承认其对保险人负有主动告知义务。如此一来,信息提供义务所被承认的范围既然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则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下的判例同样应当予以适用。不过,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于有恶意投保欺诈的投保人不必通过重要事实而仅限于“询问表”记载事项的信赖之解释对其进行保护。[46]
第二,关于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是否因询问应答模式的告知义务主义而受到限制的问题,通常认为,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将告知义务设定为“文字询问应答义务”主义,其目的一是防止投保人因错误判断重要事实而承担风险;二是由于此目的已扩展到投保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因此原则上投保人对保险人未向其提出询问的事实不负信息提供义务。但如果投保人明知该事实是重要的,即使保险人未提出询问,亦无需考虑对投保人的保护,投保人仍负有信息提供义务。[47]换言之,投保人仅在明知该事实之重要性时,才承认信息提供义务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有学者进一步强调,将信息提供义务区别于作为告知义务制度下的询问应答义务加以限制,即对于在保险人评估风险选择中未提出询问的“非典型性的”或“异常的”事实,仅当投保人知悉其重要性时,才会产生信息提供义务。[48]
同样在日本,有学者主张,对基于认识错误而承认保险合同无效的处理,有违投保人保护的立法精神,而欺诈则不然。[49]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将两者截然分开尚存疑问。换言之,正是因为认识错误与欺诈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基于意思欠缺的错误无效制度与基于意思表示瑕疵的欺诈可撤销制度的传统理论受到挑战。《日本民法典》采取了通过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成立法律行为,继而推导出权利义务变动的法律行为制度,且从权利义务变动应当基于个人意愿的意思原理来看,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话,则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50]潮见佳男教授认为,错误与欺诈都是民法中的“合意的瑕疵”相关制度,且两者最终都是基于保障“自我决定权”之理念。[51]亦即,当事人受合同约束的正当性根据,要求其是自愿决定。[52]不过,错误与欺诈都是因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不足而导致的不完整性,两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陷入认识错误的对象(重要程度)及相对方参与其中的方式(恶意行为)。[53]依此逻辑,在合同当事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收集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所需的信息,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赖另一方这一点上,可以界分错误与欺诈制度。
在此背景下,后藤卷则教授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合同双方之间存在收集信息的能力之差距这一共识的前提下,两者的界限已逐渐得以矫正。因此,根据双方信息能力的差异,信息优势方有义务向劣势方提供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所需的信息;如若一方违反此义务,则承认信息劣势方的合同撤销权。[54]概言之,错误与欺诈制度可以被视为与“信息”或“信息提供义务”有关之制度。[55]
其实,我妻荣教授很早就指出,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合同上的“附随义务”之信息提供义务,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存在较大不平衡的合同中,告知义务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课以另一方当事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具有共性。[56]另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作为保险合同的固有制度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实质上其具有与合同法中的信息提供义务理论相同的内容。因此,该理论作为合同磋商阶段的附随义务,在保险合同法中是基于“契约缔约上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法理演变而来的。[57]冲野真巳教授亦在提到告知义务制度的基础上指出:信息提供义务的存在并非只是在信息存在偏差即被承认的,而是该偏差在满足构造上的、定型的,且劣势一方不能期待对其进行收集、分析的情况时才存在的。[58]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包含了可以肯定此种情况的中心理念。
近年来,竹滨修教授也借助民法中的信息提供义务理论,在与一般合同法理论的关系下探讨告知义务制度。其主张有以下三点:(1)保险合同也是一种金融交易行为,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该合同与其他合同类型之间的共性。(2)在探讨投保人告知义务理论基础时,需要重新审视保险合同中的“射幸契约性”和“善意契约性”。(3)对于“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在仅通过一方当事人的努力难以对其矫正时,从公平角度来说,基于另一方当事人协助提供信息的要求,可以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上构建告知义务制度。[59]
四、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争辩
在“钟钢强与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存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生的保险事故(即“带病投保”),待保险合同成立后超过两年“抗辩期限”后向保险公司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60]就此,不仅涉及到《保险法》对“除斥期间”的规范问题,[61]还涉及到该如何解读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撤销权行使的关系问题,更为深层的问题还在于该如何解读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包括保险人是否有权向违反告知义务的投保人主张赔偿责任。
(一)德国法立场
1.侵权行为赔偿责任肯定说
德国的多数学说认为,在投保人就保险人风险选择时对危险事实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的情况下,因缔约过失而造成的损害概不承担责任。但如果投保人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此类行为相当于违反《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所规定的“保护他人之法律”,抑或是违反《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所规定的“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则投保人应当向保险人承担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失赔偿责任。[62]其理由在于:其一,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则(第19—22条)具有排他性,即排除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其二,该法第22条尽管明确了欺诈可撤销不为告知义务规则所排除,但并未论及缔约过失责任。[63]亦即与欺诈不同,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排除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因此并不成立缔约过失责任。换言之,保险合同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设置了诸多规范,如果承认投保人的缔约过失责任,则会使该规范“空洞化”。
德国的判例亦认为,保险合同法中有关告知义务的规则具有基于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别法地位,在投保人对危险事实未告知或不实告知时其不承担基于缔约过失法理下的损害赔偿责任。[64]但判例和通说并不否认保险人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在投保人隐藏欲引起保险事故之意图而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况下,则应构成侵权行为。[65]该案案情是,保险受益人企图杀害投保人兼被保险人(妻子)而获取保险金,自己作为妻子的代理人与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在保险受益人杀害被保险人后,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一定范围内以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仍有适用可能性。其理由如下:其一,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仅会引起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以下排他性规则的法律后果,其中还包括该法第22条明文规定的欺诈撤销权;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杀害被保险人的意图构成危险事实,是告知义务的对象。其二,不受《德国民法典》第124条撤销期间(除斥期间)所限制的“拒绝履行支付”的权利包括对于危险事实以外的欺瞒行为及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未排他对待被保险人保护的利益,与该法第16条以下的调整无关的情况。就后者而言,在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纠纷案件中,《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第826条可以与19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及以下的规定并用。本案即为上述情形。即根据该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负有对危险事实的告知义务。在本案中,保险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构成起诉对象,即构成对保险标的的侵权行为。其理由在于,保险受益人持杀害意图欺瞒保险人,以此作为工具利用被保险人致使保险人同意承保该等故意招致保险事故的人身保险合同。因此,保险受益人的行为是以“间接正犯”形式对保险人实施的投保欺诈。对此种严重违反保险合同的行为,保险受益人应当向被害人承担《德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下的“债务人对其法定代理人及履行辅助人的过错承担责任”。
2.告知义务“制裁”规定类推适用说
与此相对,少数说则认为,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未告知或不实告知,不排除基于缔约过失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施法尔斯(Schäfers)教授主张,投保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其法律效果并非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应当类推适用保险合同法中违反告知义务之“制裁”的相关规定:[66]
第一,投保人违反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如果承担由此产生对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其结果是即使在投保人仅在因过失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规定,原则上对损害恢复原状,则保险人视情况可以溯及地解除合同。在投保人无过失的情况下而违反告知义务的,则保险人既不能解除合同,亦不能根据《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条件”。也就是说,一般私法中的规定并没有充分正当地评价告知义务制度下的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关系。
第二,投保人无论是违反了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还是违反了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款之告知义务,并不影响基于《德国民法典》保护投保人的必要性。因此,即使在投保人违反了基于缔约过失之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亦应当类推适用《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2款乃至第4款、第21条及第22条的规定。[67]亦即,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法律效果,则会发生如何理解保险合同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存在意义的问题。如果在未发生告知义务而承认信息提供义务的情况下,仅限于对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事实负有信息提供义务,但在不损害保险合同法对投保人利益保护的前提下,对如何调整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所担忧。
综上,作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制裁”效果规定,德国法中除了明文保留的民法上的欺诈规定之外,因侵权行为责任之基础是建立在一般注意义务的违反之上,而非契约关系的特别注意义务,因此不受保险合同法的影响,仍然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果。故此,保险人仍有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之余地,但也不可忽略告知义务制度所规范的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日本法中的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侵权行为的关系之转变
1.“契约责任说”与“侵权行为责任说”的学说对立
日本法主要受德国法影响,学理上于明治后期(1905—1912)开始关注缔约过失理论。在讨论缔约过失问题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种类型:第一,订立以原本就无法支付为目的的合同(合同无效型);第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撕毁合同磋商(磋商挫折型);第三,合同磋商时,一方当事人未向对方提供诚实信用原则上必要的说明和信息(不当表示型);第四,合同磋商时,一方当事人因应可归责事由而损害对方生命、身体、财产及其他利益(保护利益违反型)。[68]
作为以合同磋商过程中投保人违反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从何种角度被正当化,学说认为可以以“诚实信用原则”之中心理念为根据,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说明:其一,英美法所规定的“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法理与大陆法所说的“禁反言”法理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即禁止任何人对自己先行的言行采取矛盾态度,以此阐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义务;其二,从合同磋商过程中产生的对合同相对方的期待或信赖利益保护的观点出发,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违反,将损害赔偿责任正当化。亦即,在合同磋商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期待抑或是违背自己的约定所引起的对方期待和信赖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则不被允许。[69]但上述两种观点并非相互排他,而可以并存。
诚然,如果能够确认合同磋商阶段的信息提供义务,则在解释论上承认“沉默欺诈”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亦即在就告知义务违反与缔约过失责任关系这一问题上,部分学者主张基于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损害赔偿与错误、欺诈之“合意瑕疵”制度之间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小粥太郎教授认为,依此逻辑推导出的信息提供义务,保险人以欺诈为由否定合同的约束力,不仅能起到保护信息劣势方的功能,对被侵害了自我决定的完整性权益的信息劣势方,亦为其承认损害赔偿请求权提供另一行权途径。[70]
关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中损害赔偿的关系,主要存在“契约责任说”与“侵权行为责任说”的争论。
一直以来,作为基于所谓缔约过失责任而讨论的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以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基于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支配合同当事人关系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追溯到合同磋商时,其性质上是契约责任。我妻荣教授认为,双方当事人进入合同磋商阶段,即形成合同所规制的“特殊信赖关系”,以此便产生了一方当事人保护对方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上之义务,对一方当事人违反此义务应承担比侵权行为责任更高的责任。[71]平井宜雄教授认为,在进入磋商阶段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秉承善意继续磋商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义务;对一方当事人违反此义务情况下的责任性质应当理解为与合同上的“债务不履行”责任类似的责任。[72]
与“契约责任说”相对,潮见佳男教授认为,关于合同磋商阶段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严格的《德国民法典》第823、826条不同,日本并不存在应当以契约责任处理的情况,作为侵权行为的一般问题予以处理就足够了。[73]另有观点指出,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违反信息提供义务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如果对方获得适当的信息,未订立合同;第二种是对方即使获得适当的信息,但仍未订立合同。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合意瑕疵”不能评价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则保险人可以侵权行为为由向投保人提出损害赔偿;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投保人是否构成违约责任成为问题。[74]可见,投保人应当负有的告知义务是在合同订立磋商阶段产生的“行为义务”,但该义务必须是合理的,且以合同为基础。
2.判例对“侵权行为责任说”的确认
2011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表达了行为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行为责任的立场。[75]以此判决为契机,多数学者质疑缔约过失法理的存在。在最高裁判所涉及“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违反信息提供/说明义务”的案件中,信用合作社Y处于严重的债务超支状况,尽管已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可能有破产的危险性,但Y未对X等人如实说明该情况,反而劝诱其出资,Y最终接受了X等人的出资。由于Y破产,无法对X等人返还出资份额。因此,X等人主张,Y在劝诱其出资时应当说明公司存在实质性的债务超额状况。X等人主要提出以下三点诉讼请求:一是基于Y违反说明义务的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三是以不履行出资协议上的债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审时追加),要求支付因Y的破产而无法退还的各项出资份额。一审判决驳回X等人的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以及以欺诈可撤销为由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但承认Y在出资协议订立前违反说明义务的违约责任。[76]在二审中,关于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及以欺诈可撤销为由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问题,判决与一审相同,均驳回了X等人的诉讼请求,但承认X等人的以债务不履行为由的损害赔偿请求,认为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违反说明义务构成侵权行为。[77]
对此,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认为,除因侵权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之外,不发生基于合同的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其理由在于:在合同磋商阶段,尽管诚实信用原则同样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一方当事者违反该原则下的说明义务,致使对方订立本来就不应订立的合同,使之造成损失的,此后订立的合同被定性为因违反上述说明义务而产生的结果,而以上述说明义务作为基于上述合同产生的义务与合同上的固有债务或附随义务无关,因此是一种悖理。
由上可知,一方当事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仅限于对方错误判断是否订立合同而导致的合同订立从而造成损失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订立合同是基于违反说明义务而产生的结果,以该说明义务作为基于合同产生的义务违反逻辑规则,因而不承认合同上的责任。
就此点而言,最高裁判所市川多美子调查官作出以下三点评释:(1)如果对违反说明义务承认债务不履行责任,则会产生该如何考虑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界分的问题。[78](2)在主张受到欺诈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采取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或行使合同欺诈撤销权、以错误无效为由解除合同关系要求返还不当利益的救济方法。其中,如果承认以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为基础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则会产生难以界分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然而,对于构成侵权行为的欺诈,则仅承认侵权行为责任。(3)两者虽然存在请求权竞合关系,但其适用前提均需满足欺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上的说明义务。[79]
综上,就是否进入合同关系的判断产生影响的违反信息提供、说明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判例上确立了其属于侵权行为责任。有学者指出,以往因缔约过失而被讨论为“责任”的信息提供、说明义务问题,在今天为以违反提供信息、说明义务为理由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具体到本判决,着眼于时间顺序,仅以订立合同磋商阶段为由,一概通过缔约过失法理来处理难免会产生“违和感”。除委托合同等特殊情形外,对合同当事人是否进入合同关系的判断产生影响的违反信息提供、说明义务之行为,无需适用缔约过失法理,适用侵权行为责任是可取的。[80]可以看出,投保欺诈能够得到侵权法的规制。
五、反思我国私法冲突规范的排除路径
(一)告知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的交互作用
我国《保险法》告知义务制度采用“询问应答义务”模式,在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的情况下,保险人是否能以欺诈抑或是沉默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问题有待解决。我国民法上关于沉默能否构成欺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欺诈并无明文规定,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所言“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其实已经包括“沉默隐瞒”的情形,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坚持了同样的规则。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法实质上已经承认了沉默构成欺诈。[81]根据“特别法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或“交易习惯”的要求,信息提供义务作为一种“先合同义务”,沉默亦可构成欺诈。[82]
就一般情况而言,既然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与合同法上的撤销权制度均是为解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就保险事故发生可能性之危险事实存在信息偏差,为了消减这种信息不对称或偏差,投保人就应当负有信息提供义务。[83]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若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仅仅存在信息不对称是不够的。[84]问题在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偏向于己方的信息。在这一点上,信息提供义务是在何种要件下发生,学说上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见解。[85]具体来说,在评价投保人未就危险事实向保险人告知或不实告知是否成立欺诈撤销权时,如若投保人负有提供信息的义务,那么该如何理解该义务与我国《保险法》中告知义务的关系?亦即两种制度是否可以并存?如若将我国《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相关规定视为信息提供义务的特殊规则,则在保险合同中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就具有一定的妥当性。在德国法中,由于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明文规定,投保人对危险事实的不实告知并不排除成立欺诈,因此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只要满足第二层面的故意要件就可以成立欺诈。但在“文字询问应答义务”模式框架下,关于投保人是否负有信息提供义务的讨论主要体现在,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未提出询问的事项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可以以欺诈为由撤销该保险合同?从此意义上来说,信息提供义务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不过,即使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不排除欺诈撤销权的适用,也应当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3条欺诈撤销权的解释,对投保人是否构成欺诈作出独立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规范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关系的信息提供义务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从上述告知义务制度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的关系分析亦可得出如下启示:其一,投保人不仅对保险人负有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还负有基于信息提供义务对危险事实进行告知的义务;其二,关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投保人有义务告知的事实较基于告知义务的范围要进行“限缩解释”;其三,尽管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保险法中的询问应答告知义务旨在对是否发生信息提供义务产生影响,但保险人未向投保人提出询问并不当然地否定信息提供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与基于《民法典》第500条规定的信息提供义务(缔约过失)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两者义务的内容基本相同。以此逻辑,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存在,则只要其满足故意欺诈等构成要件,就应该肯定欺诈制度的适用。理论上,“欺诈中的‘欺瞒行为’必然是以‘需要提供信息’为前提,因此信息提供义务理论中实际上包括了欺诈行为”。[86]换言之,如果承认投保人负有信息提供义务,则意味投保人未向保险人对作为该信息提供义务之“对象事实”进行告知,应当承认因投保人实施欺诈行为而保险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不过,在与违反告知义务问题存在交叉领域的案件中,比较法上亦承认保险人以欺诈为由的撤销权行使,[87]尤其是在通过故意篡改被保险人年龄,找他人代为体检等方式投保的情况下,投保人构成恶意欺诈,承认保险人撤销权之行使。[88]也就是说,在投保人对“相当重要的事实”的不告知、虚假告知的情况下,承认限缩解释欺诈适用的立场。[89]
此外,就法律的逻辑性而言,我国《保险法》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限定在保险人提出询问之事项,其规定的模式就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而言,应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从现今呈现出疾病多样性的状况看,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可能存在超出保险人的预测,患有重大疾病抑或是“带病投保”。此外,既往病史系保险实务公认的绝对危险事实,作为足以影响保险合同之成立或费率之标准的重要事实未向保险人如实告知的情况下,我国应当认识到告知义务制度与信息提供义务制度的交互作用,在评价投保人是否违反信息提供义务时,可类推适用《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例如,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曾患有重大疾病,如果保险人没有对此提出询问,投保人就不负告知义务,即使投保人在该保险合同订立时没有告知该疾病,保险人亦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该保险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违反了订立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亦即“诚信缔约义务”,构成沉默欺诈,应负缔约过失责任。[90]
(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正当化
1.对既有观点的质疑
围绕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侵权法可作为规制投保欺诈的可选路径,但鉴于侵权损害赔偿在举证责任方面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相比较为严苛,主张回归保险法本身,以应对“带病投保”等投保欺诈,借鉴德国、日本法采延长除斥期间等立场。[91]
在笔者看来,不可否认从对价平衡原则角度来说,规定更长的除斥期间有利于保险人的风险评估。但事实上,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延长至10年,是为配合《德国民法典》中欺诈撤销权之除斥期间而设。[92]在日本法中,就告知义务与欺诈的关系而言,为配合2008年《日本保险法》的实施,人身保险条款、损害保险条款均完善了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行使的相关规定,在保险人以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不退还保险费;[93]而在针对缔约过程中发生的意思表示瑕疵,保险人行使救济权利时,则受到民法撤销权行使期间的限制。[94]况且,在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纵使通过立法延长除斥期间,“在不可抗辩期间经过之后,保险人仍然无法依《德国民法典》之规定主张撤销权”。[95]是故,对延长除斥期间之提议并不具明显的实益。事实上,对于恶意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带病投保”或以欺瞒骗保之意图等原本就不具备缔结保险合同条件的投保欺诈,其名为投保、实为骗保,此情形并无关涉是否可以援引除斥期间制度这一问题。
2.以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合理性的解读
在投保人就危险事实未向保险人告知或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是否可以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这一问题上,德国的多数判例和学说原则上予以否认,但对投保人在主观性质恶劣的情况下,例外地承认保险人可以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日本近年主流的见解亦持相同立场。以此逻辑,就投保欺诈而言,如果承认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就应对损害赔偿责任予以肯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缔约过失理论具有与欺诈制度相同的功能。是故,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一种先合同义务,如若违反该义务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96]但在是否承认基于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点上却不尽然。在保险人以缔约过失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究竟是契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立法技术层面,德、日两国均采侵权责任立场,但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却不尽相同。与德国式“小的一般条款”不同,《日本民法典》第709条采用的是“大的一般条款”的侵权责任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164条采用概括立法即“大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规定了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范围,相当于《日本民法典》第709条的规定。此种立法模式可以弥补“小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难以对缔约过失问题的全面规范之不足,在违反该义务时,仅需“准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即可的主张值得肯定。
不过,就基于缔约过失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在实体法上以侵权责任为根据这一点而言,与告知义务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而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是必要条件;而因缔约过失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使投保人是轻过失也有可能产生。第二,在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致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免除保险金支付义务这一点上尤为重要,但在保险人以缔约过失为由向投保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投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使发生在保险事故之后,如果产生了相当于对保险人履行保险金支付义务的损害,则在这一点上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在此种情况下,存在通过过失相抵方式进行比例解决的可能性。第三,因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致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受到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3款“不可抗辩期间”规定的限制。与此相对,基于“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险人得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后,受三年普通诉讼时效限制。其中,在投保人仅仅是轻过失的情况下,与告知义务制度相比,承认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似仍有讨论余地。不过,从两者制度的比较来看,既然有其共通性,则至少对于投保人存在故意抑或是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投保人违反了订立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即诚信缔约义务,构成沉默欺诈,即使承认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信息提供义务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请求亦具有合理性。[97]
结论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制度与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均是为解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背景下,两者在意思表示瑕疵中存在的私法冲突问题的排除路径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负有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信息提供义务,即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路径应从两者的“排除论”转向以信息提供义务为中心的“交互作用论”。此时,在评价投保人是否违反信息提供义务这个问题上,通过德、日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危险事实产生信息提供义务的事实范围极为有限,投保人有义务告知的事实范围需要被“限缩解释”;如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是在主观性质恶劣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应当承认保险人有权以“侵权行为”为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注释】
*本文系2020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缔约过程中的信息提供义务边界与告知义务制度的协同应用问题研究”(L20BFX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学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2114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申字第2520号民事裁定书、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1732号民事判决书。
[2]ヴァイヤース=ヴァント(藤原正則=金岡京子訳)『保险契约法』(成文堂,2007年)87頁参照;岳卫、高西雅:《反保险欺诈与公序良俗理论适用问题研究——以日本法的研究为中心》,载《保险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7页以下。
[3]在《民法典》尚未实施之前,《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欺诈的法律效果为无效,《合同法》对此有所修正,其第54条第2款规定欺诈、胁迫的法律后果为可变更或者可撤销。
[4]庭田範秋『生命保険論』(有斐閣,1978年)223頁参照。
[5]John Birds,Ben Lynch,Simon Milnes,MacGillivray on Insurance Law,Sweet Maxwell Press,2015,p.631.
[6]参见山下友信『保険法(上)』(有斐閣,2018年)394—395頁;李飞:《保险法上如实告知义务之新检视》,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2页。
[7]2008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规定:“保险人以投保人欺诈性不实陈述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不受影响。”参见孙宏涛:《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8]参见仲伟珩:《论德国保险法关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规定及对我国保险法的启示》,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第80—81页。
[9]参见于海纯:《保险人撤销权:保险法中的一个制度选择及其合理性追问》,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283页以下。
[10]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11]参见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王静:《如实告知义务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核心》,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4期,第87页;孙宏涛:《我国〈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则完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98页。
[12]刘竹梅、林海权:《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疑难问题探讨》,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2期,第8页。
[13]参见前引[12],第7页。
[14]参见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第二卷·保险契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83页。
[15]参见前引[8],第77页。
[16]新井修司=金岡京子訳『ドイツ保険契約法改正専門家委員会最終報告書』(日本損害保険協会=生命保険協会,2004年)182頁参照。
[17]参见叶启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之新发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14页。
[18]参见前引[7]孙宏涛书,第66页。
[19]Vgl.,Bruck/Möller,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Bd.Ⅰ,8.Aufl.,1961,§22 Anm.11.
[20]参见张淳:《浅议对告知义务不履行与沉默欺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6卷,第221页。
[21]Vgl.,Prölss/Möller,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Bd.Ⅰ,27.Aufl.,1961,§22 Rn.4.
[22]参见前引[16],第182页。
[23]参见前引[8],第80页;前引[16]新井修司、金岡京子訳书,第157页。
[24]Vgl.,Marlow/Spuhl,Das Neue VVG kompakt,3.Aufl.,2008,S.46f.
[25]Vgl.,Wandt,Versicherungsrecht,5.Aufl.,2010,S.278.
[26]萩本修編著『一問一答·保険法』(商事法務,2009年)44—45頁;岳卫:《日本〈保险法〉的立法原则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32页。
[27]《日本保险法》第37条规定:“将成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人,在订立生命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事故发生可能有关的重要事项中,对于将成为保险人的人要求告知的事项,应当如实告知。”
[28]《日本保险法》第55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应告知事项的事实未告知,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解除生命保险合同。”
[29]江頭憲治郎『商取引法』(弘文堂,2018年)267頁;前引[6]山下友信书,第446页;土岐孝宏「告知義務違反と詐欺·錯誤」山下友信監修·編『新保険法コンメンタール(損害保険·傷害疾病保険)』(公益財団法人損害保険事業総合研究所,2021年)249—250頁参照。
[30]最高裁判所1993年7月20日判決,損害保険企画536号8頁参照。
[31]关于欺诈的法律效果,2008年《日本保险法》施行后保险公司的合同条款亦由《日本商法典》中的“欺诈无效”修改为“欺诈可撤销”。
[32]東京地方裁判所1999年12月1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1032号246頁参照。
[33]遠山聡「告知義務違反による解除」山下友信ほか編著『論点体系:保険法2』(第一法規,2014年)191—192頁参照。
[34]岡田豊基「告知義務」落合誠一ほか編『新しい保険法の理論と実務』(経済法令研究会,2008年)83頁参照。
[35]甘利公人=福田弥夫=遠山聡『ポイントレクチャー保険法』(有斐閣,2020年)78頁参照。
[36]前引[6]山下友信书,第447页;韩长印、张力毅:《故意违反告知义务与保险人合同撤销权——目的性限缩的解释视角》,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14年第44期,第15页。
[37]我妻榮『新訂民法総則(民法講義Ⅰ)』(岩波書店,1965年)310頁;我妻榮=有泉享=清水誠=田山輝明『コンメンタール民法(総則·物権·債権)(第7版)』(日本評論社,2021年)213頁。
[38]津野田一馬「記名被保険者の不実告知と任意自動車保険契約の詐欺取消し」ジュリスト3389号(2020年)92頁参照。
[39]大森忠夫『保険法(補訂版)』(有斐閣,1985年)127頁;伊藤雄司「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告知義務と詐欺·錯誤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専修大学法学研究所所報46号(2013年)59頁;前引[6]山下友信书,第447页。
[40]後藤元=三隅隆司「逆選択と保険契約」山下友信ほか編『保険法解説(生命保険·傷害疾病定額保険)』(有斐閣,2010年)272頁参照。
[41]参见前引[35],第68—69页。
[42]参见前引[29]江頭憲治郎书,第450—451页。
[43]关于欺诈类型的特点,潘阿憲「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モラル?リスクと<詐欺無効>の理論」生命保険論集145号(2003年)73頁以下参照。
[44]中西正明『保険契約の告知義務』(有斐閣,2003年)161頁。
[45]江坂春彦「告知義務違反を理由とした詐欺無効」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187号(2004年)11頁。
[46]Vgl.,Looscherlders/Pohlmann,VVG-Kommentar,2.Aufl.,2011,§22,Rn.7ff.
[47]Vgl.,Prölss/Martin,VVG-Kommentar,28.Aufl.,2010,§22,Rn.3;前引[6]李飞文,第141—142页。
[48]Vgl.,Schäfers,Das Verhältniss der vorvertraglichen Anzeigepflicht zur Culpa in contrahendo,VersR 2010,S.305f.
[49]石田満『商法Ⅳ(保険法)』(青林書院,2003年)83頁。
[50]丸山絵美子「95条·96条消契法4条(合意の瑕疵)」法学教室406号(2014年)9頁参照。
[51]潮見佳男「説明義務·情報提供義務と自己決定」判例タイムズ1178号(2005年)16—17頁参照。
[52]山本敬三「民法における<合意の瑕疵>論の展開とその検討」棚瀬孝雄編『契約法理と契約慣行』(弘文堂,1999年)149頁;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Ⅰ』(信山社,2017年)86頁参照。
[53]森田宏樹「『合意の瑕疵』の構造とその拡張理論」NBL482号(1991年)23頁;山下純司「情報の収取と錯誤の利用」法学協会雑誌119卷5号(2002年)779頁参照。
[54]横山美夏「契約締結過程における情報提供義務」安永正昭ほか監修『債権法改正と民法Ⅱ:債権総論·契約(1)』(商事法務,2018年)382頁参照。
[55]後藤卷則「情報提供義務」内田貴ほか編『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218頁参照。
[56]我妻榮『債権各論·上卷』(岩波書店,1954年)41—42頁;内田貴『民法Ⅱ·債権各論(第3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26頁参照。
[57]石田満『保険契約法の基本問題』(一粒社,1997年)179頁参照。
[58]沖野真巳「契約締結過程の規律と意思表示理論」河上正二ほか編著『消費者契約法-立法への課題』(商事法務研究会,1999年)37頁。
[59]竹濵修「保険契約と説明義務·告知義務」判例タイムズ1178号(2005年)97頁。
[60]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2114号民事判决书。
[61]参见武亦文:《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5期,第63页以下。
[62]ハイン·ケッツ=ゲルハルト·ヴァーグナー(吉村良一=中田邦博訳)『ドイツ不法行為法』(法律文化社,2011年)74頁参照。
[63]参见前引[47]Prölss/martin文,页边码第84页。
[64]Vgl.,BGH VersR 1984,630.
[65]Vgl.,BGH Urt.v.8.2.1989 VersR 1989,465.
[66]Schäfers,Das Verhältnis der vorvertraglichen Anzeigepflicht zur Culpa in contrahendo,VersR 2010,S.301(303ff).转引自叶启洲:《德国保险契约法之百年改革:要保人告知义务新制及其检讨》,载《台大法学论丛》2012年第41卷第1期,第259页。
[67]参见前引[17],第16页。
[68]北川善太郎「契約締結上の過失」契約法大系刊行委員会編『契約法大系》(第1卷)』(有斐閣,1962年)221頁参照。
[69]内田贵『契約の時代』(岩波書店,2000年)75頁参照。
[70]小粥太郎「説明義務違反による不法行為と民法理論-ワラント投資の勧誘を素材として(上)」ジュリスト1087号(1996年)118頁参照。
[71]我妻榮『債権各論(上卷)』(岩波書店,1954年)38頁参照。
[72]平井宜雄『債権各論Ⅰ(上)契約総論』(弘文堂,2008年)128頁参照。
[73]参见前引[52]潮見佳男书,第160页。
[74]参见前引[54],第128页。
[75]最高裁判所2011年4月22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65卷3号1405頁参照。本案是日本最高裁判所首次从正面就“合同磋商阶段”违反信息提供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判断的判决。
[76]大阪地方裁判所2008年1月28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1372号44頁参照。
[77]大阪高等裁判所2008年8月28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1372号34頁参照。
[78]例如,对一方当事人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如若承认债务不履行责任,即使是因欺诈订立合同而被骗取了钱财等情况,亦可追究其作为故意违反说明义务而违反合同责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
[79]市川多美子「契約の一方当事者が契約の締結に先立ち信義則上の説明義務に違反して契約の締結に関する判断に影響を及ぼすべき情報を相手方に提供しなかった場合の債務不履行の有無」法曹時報66巻6号(2014年)871頁。
[80]参见前引[52]潮見佳男书,第123页。
[81]参见牟宪魁:《说明义务违反与沉默的民事欺诈构成——以“信息上的弱者”之保护为中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82页。韩世远教授亦指出:“在我国司法解释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民法通则》第68条)。《合同法》第42条第2项(笔者注:相当于《民法典》第500条第2项)前段‘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可因此发生损害赔偿责任,实际上也肯定了消极的不作为可以构成欺诈。”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253页。
[82]参见前引[81]韩世远书,第253页;许德风:《欺诈的民法规制》,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5—6页。
[83]参见许月明、林全玲:《信息不对称、附随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0期,第37页。
[84]参见前引[54],第131页。
[85]参见尚连杰:《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5页以下。
[86]参见刘勇:《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制度竞合》,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68页;前引[55],第218页。
[87]日本近年承认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行使的案例主要有,仙台高等裁判所2012年11月22日判決,判例時報2179号141頁;大阪地方裁判所2019年5月22日判決,金融·商事判例1569号22頁。
[88]参见陈少青:《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89—90页。
[89]参见王学士:《保险人撤销权行使之实践与启示——以“法律要件论”为素材》,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73页以下。
[90]江朝国先生强调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依一般法理属于“缔结契约时之过失”。参见前引[14]。
[91]参见前引[61],第59页。
[92]Vgl.,Wandt,Versicherungsrecht,4.Aufl.,2009,Rn.816.转引自叶启洲:《德国保险契约法之百年改革:要保人告知义务新制及其检讨》,载《台大法学论丛》2012年第41卷第1期,第301页。
[93]当然,依《日本民法典》第121条,基于保险人撤销权行使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将溯及无效,保险人实现“给付免责”。
[94]《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与《日本保险法》第55条第4款规定的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相同,均为5年。前者规定“撤销权自可以追认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的,将因时效而消失”。
[95]前引[9],第293页。
[96]前引[81]韩世远书,第167页。
[97]参见前引[14],第401页。
作者:王学士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备注: 如认为侵权,可联系删除。